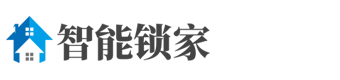那是1950年10月,鸭绿江边,夜色如墨,第40军已经越江,正准备进入朝鲜境内,敌舰突然出现在大同江口。
“等个屁。”杨成武瞪了他一眼,“敌舰靠这么近,是打咱们的!等,就全被端了。”
五门榴弹炮同时开火,炮光撕裂夜空,敌舰起火,偏航,带着火光冲向西海岸,战士们欢呼,指挥所沉默。
这是杨成武第一次被朱德当面批得毫不留情,他站在电话前,没吭声,参谋在旁边听得冷汗直冒,朱德挂断后,他一拳砸在桌子上。
第二天清晨,总参发来通报:朝鲜人民军在西海岸缴获一艘受重创的美军驱逐舰残骸。
美军舰队南撤,越过三八线,美军官方通报称“舰只因导航事故搁浅”,实际是被炮火重创。
这件事之后,军委没有处分他,也没有表扬,战场纪录只写了一句:‘敌舰自西部撤退’。
黄土岭,1939年,命他坚守待命,他直接带着一个营,主动出击,打死了日本中将阿部规秀。
按部署,应诱敌深入再打,杨成武没等,他说:“等他们进山,我这营人就剩一半了。”
他把兵埋伏在大山岭的两侧,没用重武器,没请示指挥部,三颗迫击弹后,阿部规秀中弹身亡。
朱德没吭声,几分钟后,他看着阿部的尸体,说了一句:“干得不错,但下次要报告。”
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击毙日军高级将领,日本陆军中央本部震惊,开始重新评估八路军战力。
那年,八路军武器差,兵力少,日本称他们为“山贼团体”,阿部的死,改变了这一认知。
很多人不理解:打了大胜仗,为什么还要批评?杨成武回答得直接:“战争不是看你有没有胆,是看你是不是守规矩。”
这事过去不到两年,延安整风运动开始,他成了“批评对象”,理由不是别的,还是那个词,“不经请示,个人英雄主义”。
一次大会上,有人说他“眼里只有战场,没有组织”,有人甚至建议调他离前线。
开火不用命令,是杨成武的一贯风格,而朱德,始终是那种“动手前先看全局”的人。
杨成武的“果断”,在朱德眼中,等于“危险”,而朱德的“沉稳”,在杨成武眼里,是“拖拉”。
这对组合,在整个抗战与朝鲜战场上,多次上演“打了再说”和“你不能这样”的对峙戏码。
志愿军第12军进攻文登川,敌人是美军王牌第1骑兵师,情报说敌军主力在西南,但杨成武说,不对,他们主力在北面山谷里。
杨成武没看图纸,他只看地形,他指着地图上的“V”形山口,说:“这个位置,只能是诱饵,主力要撤退,必须走这里。”
三小时后,美军空中侦察发现异常,开始火力覆盖,但为时已晚。志愿军穿插部队在夜幕下包围山口,一夜之间,打掉一个美军加强团。
三天后统计战果:缴获美军火炮39门,步枪1200余支,俘虏270人,美军报告中承认:这是整个朝鲜战事中“最痛的伏击之一”。
朱德没有再追责。杨成武也没有解释,他清楚,这场胜利用的是命赌的,一次错判,整个军都可能被包饺子。
这话传到朱德那边,没人知道他什么反应,但此后两个月,军委没有再干预他的战术部署。
没有架桥工具,没有火力支援,只有四十几个人,和一根绳子。桥长近百米,铁链湿滑,敌人在对岸架着机枪。
第二个是杨成武亲自点的,姓李,是他老部下。李兵上了铁索,嘴里咬着手榴弹,子弹在他头顶打成火网。
他没回头,爬了一半,被一枪击中肩膀,但他把手榴弹仍扔了过去,敌人炸开一角,后面战士趁机冲了上去。
杨成武听完,也没解释,他不是不知道规矩,而是知道有时候规矩,是给有时间的人定的。
朱德差点因为他“脱离部署”而要求纪律处分。还是拦了下来:“这个人打仗,有点鲁莽,但脑子快。”
意思是,只要他在场,什么部署都可能临时改。从黄土岭、泸定桥,到朝鲜前线,
但就是这种对撞,让无数次胜利,在“不能打”的时候打赢,在“不能改”的时候改变。